是枝裕和的新片《怪物》,以一種特殊的形式,爆了。
自從上线網絡,就連續三周佔據豆瓣口碑榜第一。

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它被視爲“亞洲電影的門面”。
進軍第76屆戛納電影節,放映結束後觀衆紛紛起立鼓掌,掌聲持續9分鐘(1905電影網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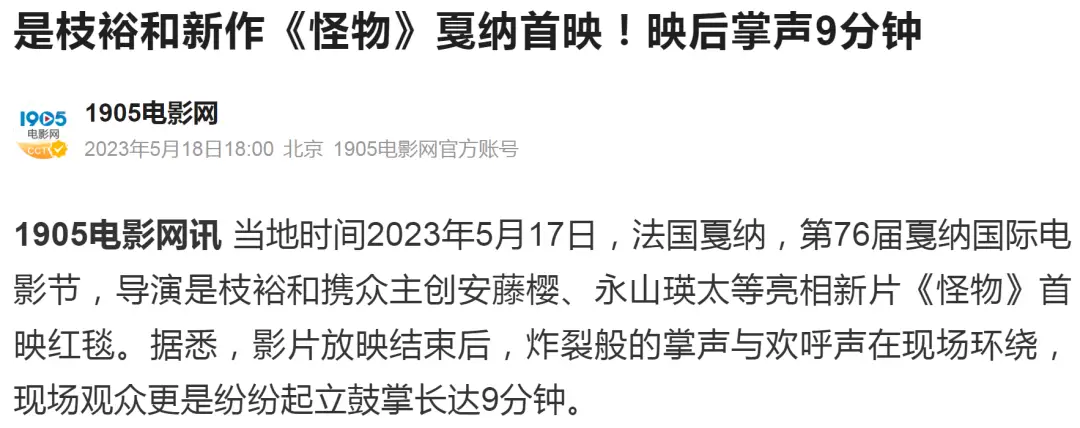
最終它獲得了長片酷兒棕櫚獎和最佳編劇獎。
影片主創陣容,也頗爲強大。
除導演外,配樂是坂本龍一,編劇是坂元裕二,主演是安藤櫻、瑛太。
一上线流媒體,就拿下了豆瓣8.7的高評分。
是枝裕和自不必說,自從《小偷家族》拿下戛納電影節金棕櫚,他基本上就是日本國寶級的電影導演了。

編劇坂元裕二也是日本影視業內鼎鼎大名的存在。
《東京愛情故事》《四重奏》《最完美的離婚》《花束般的戀愛》《在世界的中心呼喚愛》等觀衆耳熟能詳的作品都出自他手。
這種強強聯合的效果可想而知。
要么是一加一等於二,要么就是雙方太強的作者性之間會形成衝突。
在是枝裕和至今的導演生涯中,基本上他的作品都是由自己兼任導演和編劇。
這種創作路徑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影像語言和文字語言在表達上的一致性。

那么,當有一個強勢的編劇介入時,是枝裕和長久以來的作者特質是否還能夠保持呢?
這是《怪物》所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怪物》面臨的最大爭議點之一。
01
單親母親近來發現十歲的兒子麥野湊舉止十分不正常——
站在陽台上的時候突然提到什么“豬腦”;
沒由來地在浴室裏剪掉自己的頭發,問他的時候又不說話;
帶回家的保溫杯裏都是泥水和石子;甚至有一天回家,腳上只有一只鞋……
湊是那種日本電影裏常見的小男孩,沉默文靜,內向孤僻,這樣的孩子很容易成爲校園霸凌的對象。

校園霸凌無論在社會新聞中還是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都是一個十足熱點話題:《告白》《悲傷逆流成河》《少年的你》等作品中都在討論此類問題。
帶着這樣的思維慣性,我們會覺得湊在學校也遇到了類似的困難,母親也同樣如此。
湊的舉動顯得愈發不正常。
一個原本從來不會失控的孩子,开始變得暴躁,會情緒激動,還是突然半夜跑到山洞裏去待着。

當母親找到他开車帶他回家時,湊居然中途打开車門跳了出去,摔折了手臂。
想必任何一個家長遇到這種情況都會驚慌失措,恨不得立馬衝到學校一問究竟。母親也是如此,准備和校方討論湊近來種種奇怪之處,並試圖解決問題。
第一次到學校時,原本應該負責此事的校長居然轉身走了。

母親詫異,但隨後趕來的老師解釋,是因爲校長近來失去了她的孫女,所以暫時身心都無法處理此事。
見狀母親也不好說什么,只能回家等候校方的調查。
當母親再一次回到學校時,對方已經全副武裝——
由校長帶頭,包括被指控霸凌湊的班主任在內一行人全都站在辦公室裏,隨着一聲令下,就對着母親九十度鞠躬。


啊,果然是日本人啊。自然,其中班主任還要聲淚俱下地做檢討,時不時夾雜着幾個日式鞠躬。
過幾天面向公衆开研討會的時候,校方故技重施,道歉鞠躬檢討完事三件套逐一上演。
沒有什么嚴肅的調查,一切都如此浮於表面,似乎母親在進入校長辦公室時,她桌子上那張與孫女的合照擺放的角度都如此做作——正好朝向母親坐着的地方。
在母親眼中,自己天使一般脆弱敏感的兒子在學校遭受了班主任的霸凌,校方卻假道歉真強勢,試圖通過表演出道歉的姿態來強迫母親盡快讓這件事過去,口口聲聲說「事實並不重要」、「一切都是爲了保護學校」。

母親意識到了這一點,她在辦公室裏發火動怒,卻好像一拳一拳打在棉花上。

就當我們以爲影片就要進入對日本國家體制的質詢時,《怪物》卻詭異地進入了一種被大家稱之爲《羅生門》式的敘事中——
母親的視角結束後,影片轉入了班主任的視角。
在後者的視角中,湊不是被霸凌者,而是霸凌者。
他一直在霸凌同班同學星川。
02
《怪物》一共分爲三段,分別是三個視角:母親的,班主任的,以及湊和星川的。
其中,第二段是對第一段的消解和洗白——
班主任不再是變態的壞人,而是變成了一個有責任心的、有正義感的老師。
校方也不是什么日本黑校,搖身一變成了寧愿背負罵名也要維護學生的存在。

在他的眼中,是湊把星川鎖在廁所裏,是湊突然發瘋把班裏同學的書包都扔了,也是湊被同學指控虐殺了一只貓並藏了起來。
校方和他所做的一切,包括那些只有形式感的道歉,都是出於對湊和他的母親的考慮:一個單親媽媽獨自撫養孩子很不容易,而湊也到了升學的關鍵節點。
一旦這個時候他被證實存在霸凌行爲,那么湊就與學校無緣了。

但是事實究竟如何呢?湊真的在霸凌星川嗎?
隨着影片轉入第三段敘述,真相大白的同時,影片從社會問題電影立馬成爲了日版的《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星川,一個洋娃娃一樣的男孩子。他喜歡漂亮的東西,喜歡和女孩子玩,聲音輕柔,動作文雅。
這樣的孩子,最容易受到班上的排擠,原因很簡單,因爲他與衆不同。
所以,就和我們小時候大多都見到過的那種故事一樣,星川總是被班上的男生欺負。如果誰接近星川,自然而然地就會被懷疑“也有問題”。

湊是一個好孩子,他知道星川其實很好,也知道霸凌不對。但是青少年就是這樣,有時候爲了融入一個群體,就不得不开始僞裝。
所以即便湊和星川私下裏關系不錯,但表面上,湊卻很少當着別人的面和他有接觸。
甚至有的時候,迫於形勢,湊也不得不在周圍人的起哄聲中,往星川的桌子上倒兩滴墨水。

這種行爲多多少少被班主任看到過,所以他覺得湊才是那個霸凌者,星川只不過是一個“沒有男子漢氣概的男孩子”。
星川所遭受的最嚴重的霸凌其實不是來自學校,而是來自他的酒鬼父親。
他父親意識到星川的“奇怪”,意識到他喜歡男孩子這件事,所以拼命想要“治好”他。
父親總是說,星川是豬腦子,不是人,所以需要治療。

在家庭與學校的巨大壓力下,湊和星川躲進了一個世外桃源:森林裏的幾節廢棄火車車廂。
他們在這裏爲死去的小貓安葬,一起在車廂裏掛滿彩帶和玩具,一起打鬧,一起創造了一個不把他們視爲怪物的世界,一個只有彼此的世界。


影片的第三段中,《怪物》終於創造出了一句經典台詞:
男孩子知道每一朵花的名字這件事,一點都不惡心。
03
從故事內容來說,影片用一種不帶批判的多維視角,一層層撕开了日本成年人世界的遮羞布。
在那個世界裏,一切都被定義好。
所有人也都甘愿成爲這個龐大機器的驅動零件。
違背規則的,就會被視爲異類。
特別當這一切加附於兩個兒童身上,累累傷痕就會變得更加戮心。

但是,這部電影本身,是否配得上這么多贊美?
自從《怪物》首映以來,觀衆總是將它與《羅生門》放在一起比較。
這種比較本身有兩個方面的作用。
一是表明了《怪物》的劇作結構是不斷反轉的,是中性的;另一種則通過對比《羅生門》來表明《怪物》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是枝裕和是一個非常擅長創造非戲劇性情感升華的導演。
他的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並不是強情節性,而是那種從日常中透出的人性之溫暖,以及一種日本代表性的物哀精神。
通過這種共情,是枝裕和的作品得以能夠抵達一種對於日本民族性,甚至人性的質問。
所以,坂元裕二這種情節性非常強的劇本,其實不適合是枝裕和拍。
一部電影分三段,情緒就很難酝釀起來,往往是這邊情緒剛剛有點苗頭,那么情節就壓倒情緒,拉扯着故事和人物往前走。

就比如片中最具象徵意味的設置:校方不斷道歉和鞠躬的情節實際上就很有諷刺性。
但是這種情緒剛剛持續一會兒,電影就轉入了第二段敘事,告訴我們其實校方和班主任,包括校長都是爲了孩子好。
這樣說,《怪物》的問題其實就很明顯了,就是情緒與情節的衝突,文字文本與影像文本的衝突,這種衝突本身就使得《怪物》根本無法與《羅生門》相提並論。

《羅生門》告訴我們,人都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編造故事,人性之惡是原罪;
但是《怪物》想告訴我們什么?是每個人其實都是無辜的?
真的嗎?我不信。

電影從校園霸凌這一社會議題出發,卻一而再再而三爲所有人做無罪辯護——
無意中撞死孫女卻讓老公頂罪的校長是無辜的,班主任是無辜的,母親是無辜的,湊和星川是無辜的……
難道每個人都是一張白紙?這種設置無疑消減了人性本身的復雜性。

反轉和揭祕的過程如此迅速,洗白來得如此順暢,那么錯的到底是誰?
電影中的酒鬼父親,以及有些片段中的校長和班主任的行爲,完全是爲了惡才惡,爲了反襯才惡,爲了反轉才惡。
這是編劇在操控故事,不是影片人物本身的厚度。

電影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只是爲了這個劇本而存在。
《怪物》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既使得影片失去了情節的趣味性,也使得主題漂浮不定,批判之錘如同棉花做的,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這忍不住讓人懷疑,同性這個話題是不是也是被剝削性使用的一部分?
影片本身完全可以講述兩個小男孩的友誼,不需要讓兩個孩子看起來像是套着孩童面皮的異性戀大人一樣,去討論什么同性問題。

總之,在我看來,《怪物》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樣,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怪物。
一個龐大的、徒有其表的、虛張聲勢的怪物。
文/皮皮電影編輯部:童雲溪
©原創丨文章著作權:皮皮電影(ppdianying)
未經授權請勿進行任何形式的轉載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信息之目的,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如有侵權行為,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